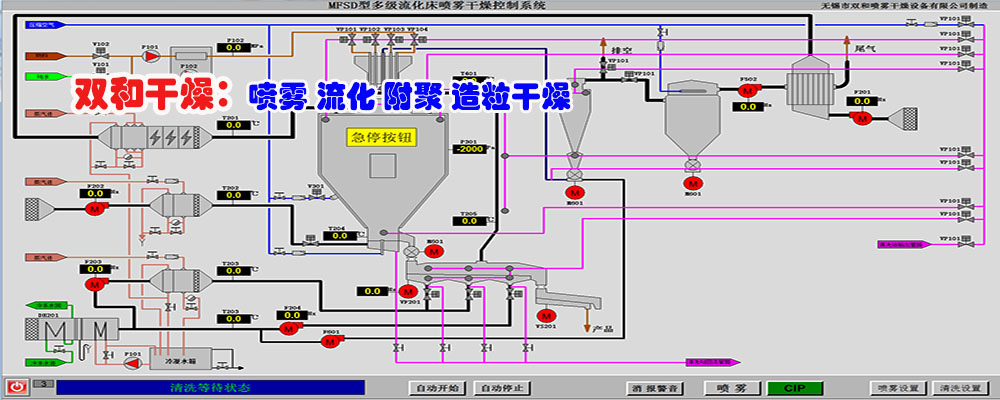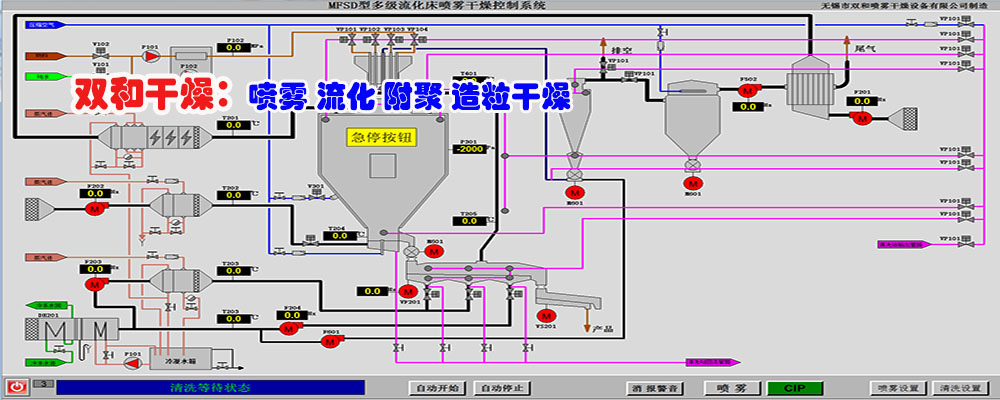|
戊戌新春,攜妻女出游,于旅次得以展讀梁秉堃先生的新作《故事中的北京人藝》。行前以此書投旅篋,原是為著消磨時(shí)光,熟料細(xì)讀之下,竟所獲甚豐,且頗有“疏瀹而心,澡雪而精神”之感,誠為一大快事!
眾所周知,北京人民藝術(shù)劇院堪稱“藝術(shù)圣壇”,建院近70年來,一向以獨(dú)特的民族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演劇風(fēng)格屹立于世界劇壇,擁有以曹禺、焦菊隱、于是之、歐陽山尊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優(yōu)秀藝術(shù)家,打磨出了《茶館》《龍須溝》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北京人》等一大批膾炙人口的優(yōu)秀戲劇作品。然而,恐怕很少有人知道,這家劇院除了有“曹頭兒”“焦先生”這樣的臺(tái)柱子,還有“老夫子”“丁道長(zhǎng)”“杜二爺”等眾多幕后英雄,而就連這些跑龍?zhí)椎娜藗儯捕几饔懈鞯膫髌妗@试隆⒎毙墙幌噍x映,大弦、小弦嘈切雜彈,使得北京人藝本身也成了一臺(tái)戲——一臺(tái)永不落幕的戲。
《故事中的北京人藝》一書所精心展現(xiàn)的,就是這一臺(tái)永不落幕的戲。作者梁秉堃先生曾在北京人藝歷任燈光師、演員、編劇,有半個(gè)多世紀(jì)的日子都是在這里度過的。他在自序中說:“而我正是北京人藝的一個(gè)‘老人’、親歷者和能動(dòng)筆桿子的‘寫家’,因此肩膀上有著義不容辭的義務(wù)與責(zé)任,把她多年的歷史,一點(diǎn)一滴地記錄下來,傳播出去……部分地為她‘修史’……”
既為修史,那就要講究史筆。依我看,梁秉堃先生的運(yùn)筆是稱得上精準(zhǔn)有力的,既不乏對(duì)劇院精魄的宏觀提煉,又富有對(duì)諸多細(xì)節(jié)的傳神刻畫。而這兩個(gè)方面,其實(shí)分別指向一條主線,前者是愛國,后者就是敬業(yè)。
北京人藝的精魄是什么?通讀全書,我們就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,這個(gè)精魄在于愛國。自建院之初,她就自覺擔(dān)起了“創(chuàng)作具有民族風(fēng)格、民族氣派的中國話劇”這一重任。書中披露,曹禺先生講過:“我們需要為一個(gè)共同的目標(biāo)奮斗,就是要建立起中國的劇場(chǎng)藝術(shù),我們一定要在社會(huì)主義道路上樹立起我們劇院的這一‘派’。”焦菊隱先生從藝幾十年,也始終是從理論和實(shí)踐的結(jié)合上,潛心執(zhí)意于解決中國話劇民族化這一大課題,其成就之卓著、貢獻(xiàn)之突出、影響之巨大,世所矚目。而就這一擔(dān)當(dāng),梁秉堃先生本人也以實(shí)際行動(dòng)給出了生動(dòng)的詮釋——1990年,梁先生執(zhí)筆的話劇《新居》上演,該劇講述的是老翻譯家澹臺(tái)文新不顧年老體衰,拼了命要把湯顯祖的名作《牡丹亭》翻譯成英文,而且堅(jiān)持高標(biāo)準(zhǔn)、高質(zhì)量,準(zhǔn)備推向英語國家,讓湯公與同時(shí)期的莎翁爭(zhēng)個(gè)高下。由此,我們當(dāng)可感受到那一顆熾熱的愛國心。
至于書中對(duì)細(xì)節(jié)的刻畫,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也真可謂不勝枚舉。先來看于是之。他23歲時(shí)出演《龍須溝》中的主角程瘋子,在排練開始前,就創(chuàng)造性地寫出了一篇6000多字的《程瘋子自傳》,使得劇中人物更加立體可感,得到了劇作者老舍先生的高度贊揚(yáng);31歲那年,他在排演《茶館》時(shí),又大膽提議增加“三個(gè)老頭撒紙錢”一幕,原來劇本上并沒有這場(chǎng)戲,于是之在排演過程中覺得戲的最后應(yīng)該讓三位老者根據(jù)自己的身世、經(jīng)歷和感悟,談?wù)劯髯詫?duì)人生的看法,遂向老舍先生提出建議,結(jié)果被欣然采納,促成了這一場(chǎng)經(jīng)典的戲。
在北京人藝,像于是之先生這樣的“戲瘋子”還有一大批。而那些沒有機(jī)會(huì)走上前臺(tái)的工作人員,也都打心眼兒里認(rèn)同“戲比天大”,表現(xiàn)出了令人感慨的敬業(yè)精神。
舞臺(tái)美術(shù)設(shè)計(jì)師“老夫子”陳永祥,為了給話劇《蔡文姬》設(shè)計(jì)穹廬,專門跑到天壇去找靈感,并在一個(gè)月中先后畫出了上百幅草圖,最終取得了被譽(yù)為創(chuàng)舉的獨(dú)特效果。
道具組組長(zhǎng)“丁道長(zhǎng)”丁里,為了給話劇《丹心譜》做道具餃子,找了濕鋸末兒來當(dāng)餡兒,把白帆布剪成圓形,當(dāng)餃子皮兒,可是怎么捏成個(gè)兒呢?這可讓他犯了難。經(jīng)過一次又一次試驗(yàn),最終他以在帆布上襯一圈細(xì)鉛絲的辦法圓滿地解決了這個(gè)問題。后來他回憶說:“眼看著成功了,我這才洗洗手吃飯。那頓飯我吃得特別香。”
負(fù)責(zé)拉大幕的“杜二爺”杜廣沛,被稱為絕人有絕活,曾多次沖上臺(tái)“救場(chǎng)”。有一次演出話劇《虎符》,當(dāng)?shù)谝荒粨Q景到第二幕時(shí),臺(tái)上布景的那棵松樹的底部突然斷裂,立不起來了。“怎么辦?觀眾等著開幕看戲,舞臺(tái)監(jiān)督急得在臺(tái)上直轉(zhuǎn)圈兒。‘杜二爺’本來正準(zhǔn)備拉幕,趕快跑了過來,認(rèn)真地看了看,便一下子跪在臺(tái)板上把松樹扶起來,再用肩膀扛著,用手扶著,以自己的身體替代了底部的木料……‘杜二爺’跪在松樹樹根處,頭上和身上蓋著厚厚的黑毛巾布,一直堅(jiān)持把這場(chǎng)20分鐘的戲演完,一動(dòng)也沒動(dòng)。事后,‘杜二爺’手麻腳酸,站都站不起來了,還捂出一身白毛汗,衣裳也濕得能擰出水來。”字里行間,讀者的敬佩之情會(huì)油然而生。
正是這樣的愛國情愫,與這樣的敬業(yè)精神,鑄就了輝煌的北京人藝,也成就了話劇的中國學(xué)派。應(yīng)該說,梁秉堃先生對(duì)這兩條主線的自覺表達(dá),是這部新作的動(dòng)人之處,也是作品得以成功的根基所在。
當(dāng)然,這部新作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遺憾。個(gè)人認(rèn)為,老舍先生雖然并非北京人藝的藝術(shù)家,但他與北京人藝的淵源如此深厚,是完全可以也完全應(yīng)當(dāng)做一篇大文章的,收入此書非但毫不突兀,反而是盡可以增光添彩、令讀者有意外之喜的。因此,筆者由衷地希望作者能在本書再版時(shí)補(bǔ)入老舍一篇。
蘇東坡詩云:“等為戲劇誰能先,我笑謂翁兒更賢。”引來作為本文題目,有兩層意思:一是呼應(yīng)書中“白發(fā)碧水童心境”“赤子天性人不老”“真情無矯飾”等語,為北京人藝的愛國與敬業(yè)點(diǎn)贊;二是以此祝賀本書的問世,并祝福北京人藝永葆赤子之心,永葆藝術(shù)生命,在弘揚(yáng)中國話劇的道路上能夠勇于超越老一輩,切實(shí)做到“兒更賢”。

|